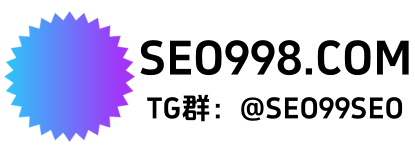游久网:吃瓜黑料最新入口-黑料不打烊吃瓜入口-李公明︱一周书记:数字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与……算法时代的生存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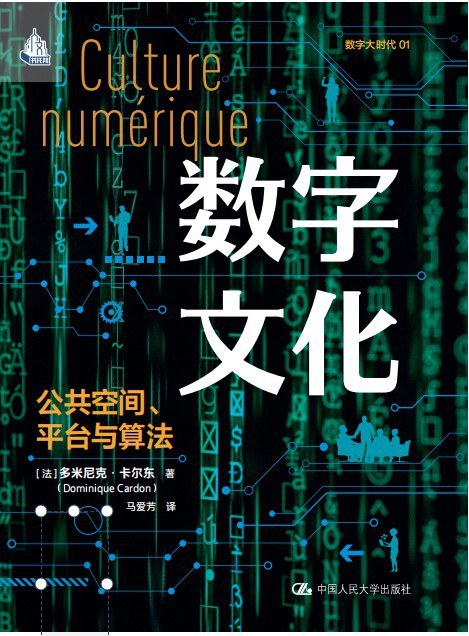
《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法] 多米尼克·卡尔东著,马爱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丨人文书托邦,2025年3月版,99.00元
读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卡尔东(Dominique Cardon)的《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Culture numerique,2019;马爱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和思考互联网发展史中的反主流文化与新经济模式的结合,结果是在对数字文化尤其是平台经济的批判性思考中的祛魅与重返互联网先锋文化的初心而产生的“复魅”的结合。该书作者的身份是巴黎政治大学社会学教授、法国著名传播学杂志《网络》(Réseaux)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成员,是法国著名的传播学、社会学与数字文化研究学者,之前曾先后出版《互联网民主》《何为数字劳工》《算法的梦想》等著作。这部《数字文化》系统地回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联网和网络普及以来人类经历的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事件,内容涉及对公共空间的解释、算法和搜索引擎对消费者的影响、数字经济催生的新经济形态以及数字文化造成的社会治理问题等等。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急速的当下,的确有必要回顾一下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进程。多米尼克·卡尔东在中文版序的开头就指出:“我们目前经历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对其建立起清晰的认识,并理解其中的关键点,因此本书系统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和万维网普及以来人类经历的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事件。”(1页)这是一种从认识历史到理解现实与判断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维,但是对于处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使用语境中的普通网络技术使用者来说,这种历史回顾与反思的意识和思维方法容易被遗忘或是觉得无暇顾及。结果是我们常常既遗失了互联网的乌托邦精神、精神游牧者的气质和转型中的公民社会建设者的信念,同时也会对数字化世界的全面降临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批判性的思考。胡泳教授为该书写的推荐语是:“在人工智能牵动的投资热潮滚滚而来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帮助读者了解互联网前世今生的著作。法国学者卡尔东的《数字文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作品,它用细腻的笔触深刻反思了互联网诞生之初所承载的梦想和热情如何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逐渐冷却、蜕变。本书是互联网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见封底)在我看来,与其他人的推荐语明显不同的是,他强调了对互联网诞生之初所承载的梦想和热情在今天遭遇冷却与蜕变的反思,这也正是我阅读该书时最关注的问题。从自由的乌托邦到被严酷监管的现实,从让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力量到在算法平台下被操控和被剥削的隐形工具,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互联网历史与现实呢?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维度并不是作者撰写该书的主要目标,作者自述“这本数字文化入门书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是以下观点:技术变革首先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我们身处的技术环境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根本变化(尤其是社会的个性化)鼓励技术成功和技术普及,从而使每个个体都能够获取信息,特别是能够在不经过把关人过滤的情况下生产信息”(中文版序,1-2页)。更具体来说,该书是在作者面向巴黎政治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讲授“数字文化”这门课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课程的教学目标首先是使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对技术的运行培养起浓厚的兴趣,其次是激发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密切关注并思考信息技术创新如何引发社会和文化变革。总而言之就是要让选修这门课的所有学生消除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专业隔阂,共同全面地、充分地认识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与历史发展。由于是对来自不同专业的本科生授课,该书在内容安排和叙述结构上都尽量做到内容详实、语言风格简明易懂。而且在书中插入了不少有关数据、示意模型等图表。还有就是,每一小节结束后都有题为“看·听·读”参考信息的版块,“它将为你打开一扇大门,让你发现一系列书籍、文章、文件或视频,使你深入了解各个主题”(5页)。应该注意的是,对这些网络文章及纸质著作、论文等阅读参考书,作者往往以最简练的一句话来点明该论文或著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很有指导性,因此非常适合作为数字文化领域的入门指南。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回顾与跨学科的认知与思考正好是相互补充的阅读视角,可以激发不同维度的深入思考。
还有就是正如“译者序”所讲到的,过去我们可能较多了解的是英语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和治理问题,对法国等非英语国家的数字实践的了解往往不深,该书正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憾。比如在谈到“公民科技:民主的民主化”这个专题的时候,为了说明一种旨在加强代议制民主机制的民主实践,作者举出了“法律生产”(la Fabrique de la loi) 网站为例子。这个网站由“公民视角”协会和巴黎政治学院媒体实验室共同发起,它允许用户跟踪议会讨论法案的情况;用户可以查看每项条款,每次修正和议员的每次投票,允许用户深入了解议员的讨论和决策程序。作者指出,“‘法律生产’网站的例子表明,作为研究工具和公民监督机制,数字技术通过向公民开放新数据,使他们获得了影响公共事务的机会。”“公民们,快来看屏幕!”(219页)这句口号让人有点眼热,我马上想起前段时间读过的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写的法国大革命编年史,书名就是《公民们》(Citixens: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9;俞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后人,无论历史的发展如何曲折复杂,有些基本底色还是会在新的转型时代中折射出来的。
从数字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来看,卡尔东在书中概括地提炼出三条主线。一是借助数字技术使个人权利获得增长,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每个个体行动的可能性增强了,这些新的表达和交流能力的效果在包括社交、政治或创新等不同领域已经被证实;二是无论是在自我组织的社区,还是在绕开传统市场的交流平台,都出现了新的集体组织形式;三是权力和价值的重新分配,数字生态系统将社会的重心转移到联网的个人和对社交网络有控制权的平台身上。作者指出以这三条主线为指引,我们将试图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试图与那些关于数字技术的肤浅讨论保持距离。这就是这本数字文化入门书的目的。我们试图表明,在日常关于手机、约会网站、脸书或地理定位的好处或坏处的那些喋喋不休背后,数字世界有它的历史、地理、社会学,有它的经济、法律和政治。要破译我们正在经历但却尚未完全理解的转型,我们需要运用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数字技术丰富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并对其进行监控。我们需要具备多样的、跨学科的知识,才能灵活和谨慎地在这个数字世界中生存,这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创造了数字技术,那么数字也在创造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数字文化,这是每个人都在倡导的事情”(3-4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关于该书主旨与研究方法的一种简练的概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译本在原著非常简练的书名“数字文化”之后加上一个副标题是比较合适的,否则一般读者对于这个“数字文化”的内涵未必能马上把握;以“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作为副标题看起来则比较契合该书后半部分(四-六章)的内容。另外,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学科的作用——卡尔东的说法是,我们需要运用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才能在这个数字世界中生存;更准确地说,在算法时代的生存指南中不可以缺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
在这篇写于2024年12月9日的中文版序中,作者针对最新的前沿发展状况提出的几个问题非常有前瞻性。第一是关于技术高速迭代这个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问题。虽然在短短几年内,Instagram和TikTok取代脸书 (Facebook,2021年改称Meta)成为西方国家年轻人钟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认为这种数字社交媒体受欢迎度的快速变化仅仅是数字技术引发的缓慢的结构性社会转型中一个相对不起眼的方面,谷歌(Google)在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或亚马逊(Amazon)在电商行业的主导地位都比社交媒体引发的“时髦”现象更稳定、更持久.因此有必要与 “时髦”保持距离,避免被数字经济激发的、一味追求新事物的文化冲昏头脑。作者确信该书所描绘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比数字技术带来的“时髦”现象要深刻得多,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关键就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深刻意义在于引起并加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版序,2-3页)。第二个问题是关于2019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虽然该书第六章详细讲述了人工智能的曲折历史,但是未能将新近发展起来的类似Chat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包含在内。作者在这篇序言中认为目前尚处在这项技术的起步阶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工具现在正逐步渗透进大众的实践和惯习之中,同时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逐渐意识到最近出现的技术创新存在多种局限性(3页)。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一种新现象的关注,那就是之前那种引领数字技术重要创新的是学生和敢于冒险的小企业的情况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而不再存在,技术创新重新回到了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大企业手中。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需要巨额投资,那些独立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小企业或小企业家已经很难获得施展才华的空间。最后的这句话我们需要运用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数字技术丰富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并对其进行监控。我们需要具备多样的、跨学科的知识,才能灵活和谨慎地在这个数字世界中生存,指出了一种新的趋势:“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改造深度和强度前所未有。如果说数字革命以前象征着与传统社会的决裂、对传统秩序的颠覆,那么如今它正在建立起新的帝国。”(4页)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在数字革命的加持下“帝国与资本”日益强大的现实与趋势。
该书第一章“互联网家谱学”全面回顾了互联网的历史,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计算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最初发展到在六十年代开发的重要项目几乎都是由军方投资进行的,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是非常独特的,从一开始就是管控和自由的结合体。“信息技术的发明与美国军队的战略密不可分,但互联网设计者们的精神指导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和合作精神,这也是当时反主流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原始的张力将一直存在于数字文化之中,它永远不会停止其影响。互联网的先驱们把精神、价值观和政治镌刻在技术中,它们恒久地定义了互联网的身份。这一切可能看起来已经是老掉牙的事了,但互联网的特殊起源——既与军事用途有关,又与自由有关——继续影响着当下的诸多辩论,这些辩论事关言论自由、知识自我组织、网络中立性、互联网的政治效应,以及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16页)关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源头以前也知道一点,却的确很少把管控与自由的结合及其紧张关系作为一种思考议题。而且,即便是对互联网的创新、分享、自由探索的精神一直怀有信念和敬意,但是对于其中的那种精神气质、言说口吻和转折性事件的氛围及意义等等也仍是了解不深、印象不鲜明的。在这方面卡尔东的叙述和评价真的是有点激动人心,我感觉其精神上的激励及审美反抗的气质完全可以视作“数字文化”的底色与初心。在此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为“黑客文化”正名。正是从每个人都努力为社群提供最好的技术解决方案这种理念催生了这种特殊的计算机文化——黑客(它来自英语单词hack,意为修修补补)。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诞生于麻省理工学院,它鼓励与计算机代码建立一种亲密、精致和富有创造性的关系。记者史蒂文·莱维(Steven Levy) 完美地将黑客伦理观概括为五点:一,黑客首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二,黑客相信信息应该是自由的。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这个信条是网络信息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息流动不受到任何阻挠,公民可以在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获取所有信息。‘没有知识开放就没有合作’的理念使信息自由成为这种先锋文化的核心主张之一”(30页);三,黑客不信任权威,总是支持去中心化,不接受别人发号施令;四,评价黑客的标准应该是他的行为,而不是学历、年龄、种族或社会地位等虚假标准;五,受科技决定论影响,黑客认为计算机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产生优美和符合审美标准的东西。黑客是一种艺术。卡尔东认为“黑客伦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极重视自由,这与黑客遭受的曲解大相径庭——他们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计算机系统,并散播病毒的剽窃者,其实有这些行为的人应被称为捣乱者。我们有必要强调黑客文化的如下特点:它是由才能卓越的人组成的贵族群体,才能是其核心价值,即通过个人能力赢得声誉,获得认可”(29-30页)。所谓贵族群体指的是精神上的贵族气质,包括价值理念与荣誉感。至于在现实生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那些作恶的网络数字技术捣乱者是否不能称作黑客,这是一个使用语境的问题。
其次是数字文化的起源问题。比起上述对黑客伦理观的概括更为激动人心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激进主义文化中嬉皮士运动与数字文化起源的关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主张之中。嬉皮士运动的目标是“改变公民个人,改变生存模式,释放人的主体性。他们想‘在不夺取权力的情况下改变社会’——可以说这句口号揭示了未来互联网政治文化的大部分主张”(36页)。“在不夺取权力的情况下改变社会”意味着放弃传统政治斗争的目标与手段,放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令人想起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一句口号:“让想象力夺权!”,很显然,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动的方案,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表征与姿态,所谓改变社会也只是一种被表达的社会愿景,真正能够实践的是改变个人的生存方式与自我认同的主体性——使个人从所有那些可能使人被异化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大学和工作场所——中解脱出来。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七十五万美国年轻人选择来到美国东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和嬉皮士营地,在流浪的社群中生活。多年前我曾去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东边的一个叫林宾(Nimbin)的隐藏在丘陵之中的小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不少从学生造反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看到的一些当年的摄影图片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情景:开放的生活,在河流中沐浴、裸泳,在草地上一边晒干身体,一边读书,这大概与卡尔东所讲的加州嬉皮士营地生活很类似吧,可以说是当年的青年造反者最后的乐园。我在小镇的街上到处看到图像古怪、色彩鲜明的涂鸦和大幅招贴画,年轻人聚集在酒吧里吹拉弹唱。我还参观了一间玻璃工艺品工厂和一间服装学校,都有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性质。镇上有一家政府的电台,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没有门卫,没有传达室,工作时只有两个人,设备简陋,但却是当地的社区文化建设中枢。想像中的那种政府部门,听起来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但在这里实现了:它属于政府,但是由人民自由地运作……这不就是卡尔东讲的“在不夺取权力的情况下改变社会”的情景吗?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旧金山周边的青年社群中出现了一本迷人的出版物,那是由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主编的《完整地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1968),该书从1968年至1972年间每年出版一次。卡尔东说:“《完整地球目录》是美国反主流文化中一件迷人的艺术品,它常被认为以书面的形式预示了先锋互联网的到来。它由各种不同的条目拼凑而成:科学书籍的摘要,生活指南,素食烹饪食谱,印度教、佛教或新时代神秘主义者的年鉴,DIY技术目录,环保建议,等等。所有条目都源自读者,其他读者在下一版中对上一版的条目进行评论。该书反映了嬉皮士社群关切的主题,但斯图尔特·布兰德也在其中加入了很多有关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内容。这本书堪称嬉皮士们的圣经,非常值得一看,因为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在它的书页中,有关个人电脑这项新技术发明的想法出现了,并且引发讨论和联想。”(36-37页)这部出版物在1971年的发行量达到了一百万册,同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卡尔东在书中加入了一幅1969年《完整地球目录》的封面和内页作为插图(37页),封面是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内页的排版图文并茂,有点像百科全书的条目。“该书通常被认为以纸质方式宣告了先锋互联网的到来。”(同上)这是阅读史上的重要时刻,是促使印刷术迈上互联网之路的精神催化力量。很令人感慨的是,那时候的嬉皮士、黑客、自由主义者对于以技术解放人类怀有纯真的梦想与信念,坚信通过探索、合作和分享而产生的新技术力量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通过增强公民的个体能力,使人们从泰勒化(Taylor System)生产线、压抑的办公室政治、守旧的家庭生活氛围中解脱出来;对于那些被政客与国家力量拽入越南战争泥潭的青年人来说,这种由新技术前景加持的自由精神使个体的反抗行动具有了新的力量感。那种精神氛围在今天想起来仍然让人心醉:一群“思想上的裸体主义者”形成了一个活泼、喧闹、富有想象力和批判性的思想空间,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性。应该注意的是,在过去有关1968年一代的青春叙事中,先锋互联网与个人电脑探索的位置和意义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卡尔东不乏激情的互联网历史叙事和对嬉皮士文化的研究正好补上重要的一笔。
但是后来发生的变化更令人唏嘘。“20世纪70年代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社群对个人微型计算机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然而,他们在争吵、逃避和拉帮结伙的影响下,很快就失去了动力。众望所归的个人解放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社群中,性别主义、家长制、不平等和富有魅惑作用的权威重新出现。许多嬉皮士带着痛苦的挫败感回家了。”(43页)可能有些嬉皮士就在那时到了澳洲那个丛林中的小镇,那里延续着“让想象力夺权”的乌托邦之梦,同时也在那里沐浴在爱河之中,那些历史照片记录了那种仍然青春的时光。“随着个人电脑的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联网电脑的出现,The Well所象征的那些电子社区就变成了避难所,用来收容70年代那些破灭了的希望。……他们对这个虚拟世界有同样的关切,即再造社会联结的纽带。嬉皮士们把他们流放和重生的梦想寄托在数字交流中。”(43-44页)于是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虚拟社群”这个词,它意味着世界分为线上与线下两个版块,线上的虚拟世界比线下的现实世界更丰富、更真实、也更有意义。虚拟世界以彻底的开放性、公开性推翻了身份等级和文化隔阂,可以重塑原来已经固化的社会关系,使自由、平等、公开的交流成为可能。当然,正如卡尔东指出的,这种愿景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The Well社群的参与者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都是白人、住在加州、受过教育、绝大多数是男性,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相同的成长史。这是在同温层中的虚拟社群,“事后看来,这些美好愿望与社群参与者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相似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时新生的信息和通信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目性,特别是当这个新生的社会宣称它将废除文化和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时。在现实中,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牢不可破,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不平等也存在于网络空间”(45页)。发展到后来,“随着大型商业平台的兴起和匿名网络的终结,随着网络的大规模使用,以及平台获取用户行为数据的愿望不断加强,要维持现实和虚拟、在线世界和离线世界的分离已经越来越困难”(47页)。应该说,“虚拟社群”中的虚拟性已经深深打下了乌托邦式的烙印,而“社群”这个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的聚落概念更加无法在网络中真的脱胎换骨。
说到这里,作者自然要谈到“互联网先驱留下的政治教训”,这是最重要的议题。
首先是产生于乌托邦想法中的“政治计划”——准确来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某种观念性的思想和倾向,卡尔东把它们归纳为五点:一,互联网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了个人解放的希望;二,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自我封闭的、个人的自私行为,相反是重视社群与交流,人们可以自行选择社群,可以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可以释放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必总是扮演社会指定的角色;三,通过彼此互联的个人推动社会变革,而不需要依靠权力机构的决定。“社会运动先驱们‘不夺取政权,但要改变社会’的口号鼓舞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许多社会运动。数字文化的政治内涵基于以下想法:彼此相连的互联网用户,即连接了互联网的个人,可以像传统政治机构一样改变社会,甚至可以比这些机构更容易、更好地改变社会。”(50页)四,相比国家和政治机构,更信任市场,自由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到了一起,这种意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今天的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就是这种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典型代表。“数字文化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之间不断摇摆,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硅谷一些大亨仍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上)但是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要打折扣了,这是卡尔东预料不到的;五,技术被赋予了可以变革社会的神奇力量。数字创新被认为可以推翻等级制,使传统机构失灵,并撼动传统的社会秩序。技术真正被认为是政治行动的工具。硅谷公司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数字技术成了一种拯救的力量。依靠社交网络、大数据、移动应用、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难题。(同上)
其次是通过引述昌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 的当代社会学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1999)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认识六十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为何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向网络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过渡。当时所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生产力不断下降,资本和劳动的配置遭到质疑,在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看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抗议活动包含了对社会的两种批判: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批判,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和社会正义;另一种是“艺术”意义上的批判,抗议者提倡社会关系的真实性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经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需求,但是可以满足第二种需求,途径就是把公民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渴望融入公司的管理模式之中(51-52页)。能够把商业模式的转型、对经济效益的最大追求与激励 “酷炫”和“个人自主性”等概念联结在一起,这真是资本主义的天才创造。卡尔东热情洋溢地赞扬数字文化的创造性所带来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重视人的个性和才能、宣扬机会平等、文化资本增加、自由选择归属的群体、体验的不断加快并叠加等等。每年八月底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举行的“火人节”就是加州高科技公司的员工的精神宣泄和数字乌托邦文化的象征性节日,他们施展创造性、重塑社会关系、沉浸在世外桃源般的奇境之中。但是同时也暴露出矛盾性的特征:“既富有创造性又充满商业气息,既是小社群的又是全球性的,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带点卖弄色彩,既是开放的又是不平等的。这表明互联网先驱们不仅留下了关于网络的乌托邦世界,而且遗留下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东西。当互联网这个最初只有少数人使用的工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规模庞大的网络时,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就公开表现了出来。”(53页)从前面这些论述的视角和深度来看,说是“政治教训”有点谈不上,而更应该看作是互联网乌托邦文化的初心及其内在矛盾。
在第三章“参与式文化和社交媒体”中,关于社交媒体中的身份和言论监管问题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存在于互联网文化中的内在矛盾性。卡尔东指出,“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在网络世界依然存在。与社会底层人群相比,社会上层人群在网上的朋友圈范围更广,而且在社会地位和地理分布上更多样。相反,社会底层人群的朋友圈更狭窄、更单一,且局限于较小的区域。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分配上的不平等为某些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数字身份塑造得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参加娱乐活动、约会、别具一格的社交经历等。措辞、分享内容的类型、兴趣爱好、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回复他人评论的方式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140页)说到底,还是人的线下世界决定了他(她)的线上世界,后者在总体上仍然在复刻前者的主要特征,谁也无法做到真的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进入另一片新的天地。至于对网络言论的监管问题,谁也无法否认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混乱甚至违法的乱象。问题是对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的理解,按照卡尔东的表述,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法外之地”的问题,而且立法者——在我看来在更多的语境中是执法者——对网络言论的干预越来越精准、详细(160页)。具体情况视不同国情语境而有很大区别,“在一些学者(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看来,互联网原本是一种可以使反抗性话语得到释放的工具,而现在它甚至成为一种用来发现并囚禁反政府主义者的最有效工具”(161-162页)。
第四章“数字公共空间”论述了“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互联网民主这种三分局面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数字科技起到的转型作用。我们将看到数字科技对代议制民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参与式民主所起的作用尚未清晰,但在互联网民主的框架下,数字科技的作用是崭新的、可以改变现状的。很少有技术创新会像互联网一样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期待”(173页)。在这里当然就又回到互联网先锋们所推崇的去中心化、水平化和自我组织的自发性,由此设想出一种反主流的政治模型,它更新了代议制民主下的各种陈旧形式。但是问题与矛盾不但同样存在,而且更为尖锐:“在被赋予了众多希冀之后,数字技术又使人们失望。数字技术具有模糊性,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也各不相同,因此数字技术有时也会促进中心化和控制机制的出现。随着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崛起,网民的言论自由逐渐受制于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担忧。借助数字技术,威权国家对反政府主义者和普通公民的政治监控越来越巧妙、精准;甚至在那些受人尊敬的民主国家,对特定人群的监听也发展起来。……在网络上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汇聚了民众对政府和机构的愤怒和抗议。对许多人来说,网络蕴含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为对代议制民主的威胁。”(174-175页)从最近的国际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来看,更加暴露出互联网政治的矛盾性质和复杂机制。但是卡尔东并没有失去对技术可行性的信心,他指出:“所有这些变化和矛盾并没有阻碍新一代公民发展‘公民技术’(civic tech) 的热情和想象力。公民技术是指在互联社会中开发出来的一系列工具和服务,旨在改善民主辩论和公共政策。对公民技术的创新性试验正在全面展开。在前辈们的眼中,民主机器似乎已经瘫痪和腐朽,但互联网民主仍然充满了新的可能性。”(175页)
从热情洋溢的回顾到清醒的批判性思考,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卡尔东的最后陈词很值得引述:“本书在数字技术先驱们的喜悦中开篇,在监控社会的噩梦中收尾。先驱们梦想着有一种技术能使社会联结起来,能让人们共享知识,能将共享的知识转化为共同财富。先驱们帮助公众释放出自己的个性,在网络上表达自己;他们帮助扩大了公共空间;他们催生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但如今,恐慌成了人们讨论数字大变革的基调。有人说网络已经被商品化了,有人说人类受到算法的监控和操纵。数字世界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它被视为一个控制人类行为的庞大系统,一个各种病态和上瘾行为的载体,一个监视我们一举一动的‘老大哥’。网络非但没有创造新的自由,反而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然而数字空间的活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尽管这种活力有时会被大型平台的中心地位掩盖。要保持数字空间的活力,用户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持好奇心,从而避开信息的主要岔路口,避开搜索引擎结果的首页,避开社交网络的上瘾行为。数字空间总是充斥着特殊的、创新的、奇特的或丰富的体验。……网络的发展历程铺满了大胆、创新、奇特和富有开创性的倡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活力会停滞,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GAFA的主导地位会将这种活力完全封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人员、网络社群、政府部门尤其是网民共同努力,维护由网络先驱们开创的数字空间的活力,它是本能的、多声部的、不可阻挡的。”(330页)
即便对于非技术主义者来说,对数字技术与文化的活力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还是有认识和有信心的。另一方面,无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凶猛、新的数字帝国看起来如何威力无穷,但是人类的命运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类自己如何做出选择和采取何种引领技术发展的实践方式。